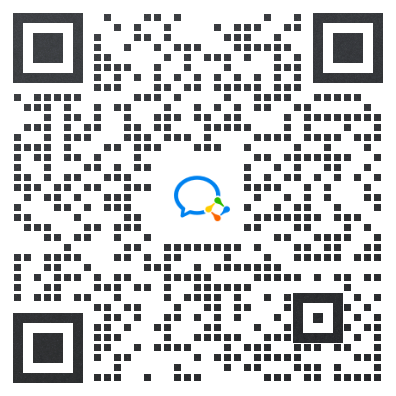《藏书》《续藏书》是明代李贽的主要著作。李贽一生写下了大量的史学著作,其中他最重视的是《藏书》,自称“此吾精神心术所系,法家传爰之书”。李贽自知此书与世不相宜,说“吾姑书之而姑藏之,以俟夫千百世之下有知我者”,故取名为《藏书》。
《藏书》共68卷,取材于历代正史,用纪传体载录了自战国至元末的历史人物约800名。李贽按自己的观点把这些历史人物加以分类,对一些类目写了总论,对一些人物、事件和言论写了专论或简短评语,评论尖锐、泼辣,富于批判精神。《续藏书》为《藏书》的续集,由王维俨于李贽去世7年后刊,共27卷,主要取材于明代的人物传记和文集,载录了明神宗以前明代人物约400名。《藏书》《续藏书》中,李贽对史书体例和编排进行了创造,对载录的历史人物做了与传统见解不同的评价,集中体现了李贽的史学理念。
昭彰事实,垂鉴后世:对史书体例的创造。李贽在史学理念方面的首要贡献,在于他第一次明确地从经学“袪魅”的角度,提出并论证了“六经皆史”“经与史相为表里”,主张历史学研究应史论结合,注重揭示兴亡治乱的规律,以更好发挥其“昭彰事实,垂鉴后世”的社会功能,为“志在救时”的实践目的服务。
遵循着史论结合、昭彰事实、垂鉴后世的思路,李贽在史书体例上有一个重要创造,即把“本纪”与“世家”合二为一,创造“世纪”体。这一创造,打破了传统的“书君上以显国统”的“本纪”体例,有利于人们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获得“治平之事与用人之方”的启迪。一方面,那些虽然失败却影响过历史进程的英雄人物,纷纷被写入了“世纪”中。如陈胜和项羽,李贽专门为其写了传记《匹夫首倡》和《英雄草创》。另一方面,《藏书》《续藏书》着重记叙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帝王的事迹,不是任何帝王都可以在“世纪”中占有一席之地。如西汉,主要记述了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5位帝王的事迹,至于元、成、哀、平诸帝,则被认为“此不足称帝矣”,附于宣帝之下一笔带过。
《藏书》的列传部分也与传统的纪传体史书的体例在分类上有很大不同,其列传分为大臣、名臣、儒臣、武臣、贼臣、亲臣、近臣、外臣八大类。从《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后论》的说明来看,列传各类编排的顺序,即形成历史由治而乱的过程。李贽认为儒臣为治终乱始的关键,其云:“儒臣实不可以治天下国家。”在举用儒臣前,治世有大臣、名臣,无论君王是否为圣明之主,举用大臣便得以辅天下而至太平,使百姓得到安养。名臣虽未必知学然实有学者,凭其才能可至守成治世之功。李贽所谓之儒臣,其功皆在文学,故无益于天下,又以明哲保身处世,故天下无臣之事功,便日渐衰退至乱世。世乱则武臣必出,贼臣觊觎天下,亲臣、近臣谄佞于君臣之间以取其利。天下至于大乱,大臣无所作为,隐于江湖,是以外臣为终。从《藏书》的这一史学体例来看,李贽的根本宗旨就是要从历史事实中总结中国历代王朝从兴盛走向衰落的规律性,探求国家富强的道路。
道不虚谈,注重实效:以事功为主的记载。《藏书》《续藏书》中,李贽判断是非的标准以实效为准,而非道学者所依据的圣门古训。他在书中开宗明义地反对以孔子的言论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他高度赞扬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称其为“千古一帝”;他赞赏法家革新进步的思想,给予著名法家人物及具有改革理念的政治家比较高的评价。李贽说:“夫当行而后言,非通于道者不能;可行而后言,非深于学者不能……真所谓通于道、深于学者也,故能洁己裕人,公恕并用,其言之而当行而可行者乎……实学也。”可以看出,李贽的“实学”理念包含了“当行”和“可行”两种属性,体现了“道不虚谈,注重实效”的标准。
《藏书》《续藏书》中对于人物、事迹的记载皆是以事功为主,由其篇幅之长短可见其事功之多寡。例如,在世纪对于历代君王的描述,事功如汉武帝者,其篇幅颇长,且所举皆为武功;无事功如汉元帝者,篇幅很短,甚至仅一笔带过,无从记录。由此可见,《藏书》《续藏书》中历史人物之定位,取决于事功的高低。
李贽把“童心说”推广和运用于历史学研究领域,提出了“论赞须具旷古只眼”。他总是把有真才实学的士大夫和正统儒者对比,《藏书》对儒臣的批判无所不在。《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后论》云:“呜呼!受人家国之托者,慎无刻舟求剑,托名为儒,求治而反以乱。而使世之真才实学,大贤上圣,皆终身空室蓬户已也。则儒者之不可以治国家,信矣。”李贽说《藏书》“凿凿皆治平之事与用人之方”,这段话正是他对《藏书》的理论总结。
民贵君轻,以质救文:对治乱循环的突破。“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循环在中国历史上一再上演。李贽在《藏书》中展现了对这种治乱循环的表述:“一治一乱若循环。自战国以来,不知凡几治几乱矣。”他认为自战国以来,中国朝代便在治乱之中不断循环,而造成治乱的主因为“文”与“质”的消长。《世纪总论》说:“夫人生斯世,惟是质文两者。两者之生,原于治乱。其质也,乱之终而治之始也,乃其中心之不得不质者也,非矫也。其积渐而至于文也,治之极而乱之兆也,乃其中心之不能不文者也。皆忠也。”
李贽认为,历史治乱循环不断,乃在于君臣不能守其质朴本心。因此,李贽提出“以质救文”,希望能挣脱治乱循环的必然。李贽所强调的君臣之事功,其在于能够使天下百姓得到安养。李贽认为百姓是国家的基础,君臣的作为皆需从百姓出发,因此不可有为一己之私欲的奢靡行为。从历代治乱循环的观察,凡君王能守其质朴本心者,其能以国家为己任,用心之处皆为百姓安居乐业、民心归顺,政策自然通行,危乱无从发生。
审时度势,适时变通:识主建功的时势相对论。求变是李贽《藏书》的主旨之一,他在《藏书·世纪列传总目》中提出了两个命题:一是“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一也”;二是“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时移则事移,不同的阶段,是非标准也应随之更迭。因此,李贽青睐那些审时度势适时变通的士大夫们。
李贽在历史治乱循环的观察中了解到,圣贤之君不可常遇,因此在一质一文的变易中,治乱随之嬗替。为顺应此种变易,李贽认为为臣者应随时势权宜,以求适得其所,建功于天下国家。《秦始皇帝传》云:“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李贽于其下评点曰:“‘各以治’三字甚可贵。”李贽以三代圣主之治表示顺势之重要,他认为时势是相对而生,因此不能受制于定法,为臣者居于朝必不能以安其身为满足。《德业儒臣后论》云:“虽有孔子之圣,苟无司寇之任,相事之摄,必不能一日安其身于鲁也决矣。此自然之理,必至之符,非可以架空而臆说也。”李贽借由孔子表明,为臣者所事之君、所处之势,应能展其才识,得以为之建功。若只是安然于朝,不得其用,则应断然罢去,归顺于明主以求用。即使是圣人,也是在审时度势适时变通中成长起来的。
遇邦无道,吏隐为终:自我理想的寄托。《藏书》是李贽于晚年的发愤之作,此时期李贽的史学理念已臻成熟,人生历练积累丰厚,因此无论是社会观察或历史观察,都有其深刻的思考。然碍于明代的政治风气与李贽作风相斥,其抱负无处伸展,是以寄托《藏书》《续藏书》,借由历史的舞台展现其理想。从他对《外臣传》人物的评论可见,李贽认为人既有才,则应为朝政建立事业,以安养天下百姓。但若是形势迫于不遇明主,则隐于江湖待明主而出。
据历史循环论,一质一文终致一治一乱,《世纪总论》云:“天下乱则贤人隐,故以外臣终焉。”天下乱则无道,贤人不得用则隐。有志之贤臣出走,徒留求名之儒臣,已然是国家衰亡之势,因此李贽以外臣为治乱之终。李贽将外臣分为时隐、身隐、心隐、吏隐。李贽认为有才之人皆待贤君举用,因此外臣隐于外是有其不得不隐之因。时隐外臣者,见君无用人之明,具真才实学之贤人,因时不得其势则隐于江湖,以保其全身。李贽认为所学所为一旦陷于名利之中,误以得名即是有德,而专学于名,反不知有具体作为,是失其本性。李贽《藏书》以吏隐为终,是德行合一的最佳表现,亦是其史学理念的最高原则。
张燕红
来源:学习时报

微信扫一扫在手机阅读、分享本文